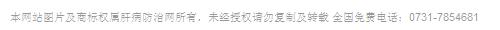年5月,看了美国著名记者、作家琼·狄迪恩的作品《奇想之年》,该书获年美国国家图书奖,书中讲述了她的丈夫突然离世和女儿重病住院那一年的生活和层层叠叠无以诉说的心路历程。开头是这样两句话:人生在一刹那改变,那一刹那稀松平常。
在写这篇札记时,我不得不佩服琼·狄迪恩,她怎么能在经历了那样的遭遇后,还能细致入微栩栩如生的描写那些不堪回首的过程?甚至是娓娓道来?我做不到,我不想重复,不想再次面对,写到那一个个抢救治疗的日子时,我觉得很挣扎,很抗拒,“笔头”都是涩的,只是为了完成这篇札记,为了一种寄托,一截一截磕磕巴巴的硬写下来。或许,这也是一种真实。
国庆期间,胡叠几个来看我,我们在屋顶花园喝茶聊天,我给她看了7月中旬老丁、郑铮、刘建一我们在屋顶花园喝茶聊天的照片,胡叠叹息道:心里好难受,恍如隔世……
对于老丁来说,他的世界从7月21号彻底改变……
(年1月,老丁在墨西哥科苏梅尔岛玛雅文明遗址前)
年7月21号早上起来,感觉也是个稀松平常的日子。
像往日一样,我削了苹果,煮好了鸡蛋。也像往日一样,老丁赖了一会儿床才起来。印象中他那天心情不错,笑脸盈盈的拿起苹果吃。本来,我们计划9月份去意大利深度游,我尤其想去看庞贝古城。准备到旅行社签合同时我的退休证却找不到了,而且还必须要退休证。打电话到单位人事处补办,但已经放暑假,主办此事的工作人员刚刚回老家。无奈,我说,要不我们到肯尼亚看动物大迁徙吧。到肯尼亚不需要签证,更不需要退休证。而且同一条线路,8月份的价格和9月份相差几乎一倍。
老丁自然没有意见。
我拿出小电脑,坐到餐桌边,一边开电脑一边说:“我再来看看具体行程,确认后给旅行社打电话。”
大约9点的时候,老丁吃完了两个鸡蛋,他坐在沙发上说:“我头有点晕,我去床上躺躺。”
我说:“你去躺吧。”心想,反正也没啥事儿。
他站了起来,又坐下了,说:“不行,我怎么头还疼。”
我说:“那你就躺到沙发上吧。”
直到这个时候,我还没有一丝一毫的预感,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他在沙发上躺下了,我过来关了空调,又开了另一间屋子里的空调,主要是不想让风对着他吹。然后,我又回到电脑前,还没找到肯尼亚的页面,老丁突然说:“快,快叫救护车,我怎么觉得手脚不听使唤了,我是不是又中风了。”
他原来中过两次风,肯定清楚发病时的感觉。我一听,也不敢耽误,赶紧打电话。一紧张,第一次拨的是,对方一应答,我赶紧又拨,回复说这个区域的救护车已派出,要我打。我马上又打,那边说会立即赶过来。我这时找来他的外衣长裤给他穿上,又找了一张上面有几万元钱的银行卡带上,找到他的“蓝本”和病历,然后给公寓前台打了个电话,要他们待救护车来了打开栅栏杆,并派人上来帮帮我。
在等救护车的过程中,我还搀扶着他上了一次卫生间。从卫生间出来坐到沙发上,老丁还说:“救护车怎么还不来呀,快来救我呀!”
人都是有直感的,看来老丁知道自己这次犯病的严重性。
我这时只好一边安慰他一边和急救车上的医生打电话催促。可救护车不是守在你家门口呀,开过来是需要时间的。
很快,公寓来了两个工作人员,推着一把轮椅。他们有经验,知道救护车上的那个担架床进不了电梯。接着,救护车上的医生也赶到了,给他量了血压,又埋好了输液的针头,把他扶上轮椅,推到下面后上了担架,上车后输上液,连上了监视器。
直到这个时候,老丁还在和医生打招呼,甚至想表现的轻松风趣一点,所以我不是太紧张,我以为他像前两次中风那样,医院就好了。他年和年中过两次风,都安然过关,除了左嘴角和左手指有点麻木,基本没留下后遗症。现在回想起来,正是这两次没有后遗症的幸运,使我和他,尤其是他自己,对身体很自信,平时根本不注意,酒照喝,药照样想吃就吃,不想吃就不吃,也不锻炼身体,还贪凉,喜欢吹空调吃各种冰激凌。而我平时除了参加形体训练,还常到公园走路,每次五公里,拉他去走过,走了一圈儿就逃掉了。楼下有一家磁疗店,据说有疏通血管,改善微循环的作用,我坚持做了一年多,怎么跟他说都不去做,有一次好不容易拉到门口,又不进去了。还有喝酒,他是这样对我说的:我没有别的爱好,就是喜欢喝点酒,喝酒你就别管我了行吗?
哪里知道,他的这种固执,会有这样的后果!
救护车很快到医院,到了急诊科,交了费就去拍了片子,是小脑出血!出血量是28毫升!急诊科的两位年轻大夫建议马上做开颅手术,做不做由我来决定。我问:开颅会怎么样?他们面无表情的说:有很大的可能就死在手术台上。
多大可能?
百分之九十以上。
我这时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死?死亡就这样猝不及防的来临了吗?生命真的如此脆弱!心一下子揪了起来。
事后回忆起来,对我们的医疗程序还是有些怨言。当病人家属突然面临生死抉择的时候,是否可以态度温和一点?是否可以多解释几句?是否可以把各种可能性都说的更清楚一点?是否应有心理帮助?或者你们给出一个坚定明确的医疗建议也好,让一个缺乏医疗知识的人在突发情况下来决断自己亲人的生死存亡,是否有问题?
郑铮讲过在美国时她丈夫刘建一做心脏手术的情景。事先医生和家属充分沟通;手术过程中每一个步骤都及时告知;还有教会志愿者陪同安抚;还有舒适安静的休息室……而在我们这里,医院,各行各业离人性化规范化都相距甚远。
我们这里没有什么交流,医生只是拿着表问我签不签字。
我签还是不签?
这个时候,老丁还躺在急救室里笑呢。
几个小时后他就要变成一具……
不!不!不!
我没有在医生递过来的表上签字。我说,给我一点时间,我打几个电话。
给胡叠、罗琦、儿子靖靖还有老友文志和他当医生的女儿萌萌打了几个电话,得到一个重要信息:医院,医院是医院。我这时只有一个想法了,我要救他,我要把医院!最好的!
我又打电话叫救护车,然后从北城到南城,不知道这个穿越过程中会发生什么,那几十分钟,我是紧张万分了。
医院人满为患,车辆的出入都很艰难,中国人又没有给救护车让路的素质。当时那个急呀!
好不容易开到急诊室,又是一阵的忙乱。原来,救护车上的担架床不能推进抢救室,必须先医院的床才能推进去。只有跑来跑去的一番折腾。
进了抢救室,把老丁搬到病床上,我才松了一口气:到了这里,他应该安全了吧!医院呀!
没等我把这口气松完,就是一阵呼来喊去,要我缴费的,要我签字的,还要推去做CT,救护车上的医生也拿着发票追着要我交钱,这里面签的包括病危通知书,我那时真是头都大了。而这时,老丁的衣服被脱光了,还要插尿管。他这时还有意识,肯定挣扎反抗,大声的喊我:杨菁!杨肇菁!
我在里面签字,听着他在外面喊叫,我有什么办法?这个时候,只有把他交给医生了。
好不容易,办好了该办的手续,但我也不能呆在抢救室了。出去的时候,我看了看他,估计给他打了镇定的针,他睡着了,脸色正常,看不出他正处于危险的境地。
出来后靠在椅子上,看见抢救室外面挂的电子钟,才知道已经1点多钟了。从早上9点多到现在,多么可怕的4个多小时。这时,胡叠赶来了,给我送来了午饭和水。问我带了什么东西,缺哪些东西。我哪里知道老丁是这种情况,什么都没带,连必须吃的药也没带。
看着我吃了饭,胡叠说她回去一趟,给我带些必备的东西再过来。
后来,她不仅带来了晚饭和一些生活用品,还带了一个沙发靠垫和毛巾被,医院值守是非常需要的。抢救室里的都是危重病人,病人家属必须24小时在外面值守,以便随时随地和医生沟通,因为病人有可能分分钟就“挂”了。
医院,我让她回去了,说我一个人没问题。
在抢救室外面的椅子上坐了一会儿,觉得很疲惫,浑身酸痛,东歪西靠的,怎么坐都觉得不舒服,只有闭着眼睛,听着周围来来去去形形色色的各种声音,强迫自己要睡一会儿,不然明天就抗不住了。
夜里,迷迷糊糊之中,听到了喊“丁道希”,我一惊,怎么啦?随即清醒,抬眼一看,电子钟显示是3点15分,这个时候喊绝对不是好事。完了,完了,我以为老丁完了,那一、二十米路是怎么走过去的,脑子里是空白,估计那个瞬间被恐惧席卷了。我到了抢救室门口,看见一个胖胖的年轻女医生站在那里,递给我一张发票说:这张发票要退费。
说完递给我扭身进去关上了门。
退费?你TM半夜三点多喊叫危重病人的家属就是为了一张退费的单子!你想过被喊家属的感受吗?那真是心惊肉跳的,若是有心脏病肯定吓坏了!真想抽她一耳光!经常看到医患关系紧张的报道,我想,双方都要反思。
后来某天上午,琳达听到电话里医生问来了几个病人家属,要我们马上到抢救室时,腿都软了,磕磕绊绊的跑过去,结果进去一问,只是要我们推老丁去做CT。
她捂着心口说:吓死我了,吓死我了。
我说,我已经被吓过了,不怕了。
医生可能每天面对生与死,习惯了,无所谓了。
可谁能对自己家人抱无所谓的态度?
22号早上7点多,靖靖从武汉赶过来了。他听我说了他爸的情况后说应该开颅。因为几年前武汉著名的评书表演艺术家何祚欢脑出血住院,医院值守的也有他。何祚欢和老丁是中师同学,靖靖结婚,何是主婚人。靖靖说何做了开颅手术后两个多小时就醒了,还说饿了要吃东西。
听他说了,我和靖靖当即找到神经外科的医生要求给老丁做开颅手术。那个医生说,老丁的出血位置不好,接近脑干,且具体出血点情况并不清晰,开颅很凶险的。一句话,不能开颅。后来,神经内科的医生建议做开颅手续,这时,老丁的小弟弟道纯也从武汉赶来了,我们又一次到神经外科提出开颅的要求,都被这位医生拒绝了。
心里真的很纳闷,医院说应该开颅,医院说不能开颅呢?为什么神经内科说应该开颅,神经外科又拒绝呢?
我把老丁的片子拍照发给了他在美国的妹妹琳达。琳达找她认识的医生朋友看了,也说开颅基本就是在手术台上下不来了。
最后只有“选择”保守治疗。
第二天的时候,老丁的意识还比较清晰,靖靖进去看他时,还知道问孙子祥祥的情况,还说医生把他当神经病对待,估计是怕他乱抓,把他的手脚给固定了,也是对脱光他的衣服耿耿于怀。
第三天,他的意识已经模糊了,我问他我是谁时,他含含糊糊的说了句:你是我爱人。后来就没有意识了。
靖靖来后,医院对面的如家酒店。医院,周围的酒店人满为患,价格不菲。最低的如家,一晚元。医院值守,我赶紧回去带了换洗衣服和药品,住到了胡叠家。医院还比较近。没想到,一直说到她家住着玩儿,最后是以这种方式,而且一住就是20天。
第五天,医院要我们多来几个家属,推他去复查CT。靖靖值了一晚上的夜班,刚回到对面的酒店睡觉,只好又把他叫来了。后来,我、道纯和靖靖还有一个护士推着他去拍片。从抢救室过去要拐几个弯,走廊上全是病床、病人,看病的人,陪护的人,还有凳子杂物,医院,如此混乱不堪。老丁这时虽然没有意识,但对把他的手固定起来非常抗拒,一路上都在挣扎,都在不停地扯手上的布带子,一刻也没停,完全是下意识。
进去拍片子,还要让家属呆在里面穿上一件沉重的防护服陪同,前两次都是我在里面接受辐射,这一次,护士说了:儿子留下吧。我前后在里面陪同了5次,最长的一次拍了17张片子,也不知被辐射到什么程度。
这一次拍片的结果令人绝望,出血量增加,成了41毫升,且SAH加重。在网上查了,SAH是蛛网膜下腔出血。下午两点进抢救室探视时,医生说:可能就这几天了,做好准备吧。
“做准备”是什么意思,大家心里都明白。我,靖靖,道纯,出来后坐在等候厅的椅子上,都没有说话。那天,我第一次觉得腿软,坐在那里流泪了。
道纯说:该通知的你要通知了吧。
按我的性格,除了家人,我不想在最后结果出来前告诉其他人,一是不想打扰人,二是说了有什么用呢?三是他真的要死了吗?我的直觉还没出现这样的第六感。
前两天,妹妹妹夫们打电话要来京,我一直没答应,我觉得还没到那个时候,他们来了也帮不上什么忙。我希望在我真的需要帮助的时候他们再来。
可现在?如果不通知,万一……老丁的朋友一个都没有来,是不是也是个遗憾呢?
为了不留下遗憾,我才打电话告诉了小肖朱竞志云陈燕小玲小兵老金于青郑铮建一文夫小潘老赵叶梅柏林李晨郑飞等一些好友来见见老丁的“最后一面”。也给方华打了电话,请她帮忙通知文联老干局。给江淮通话时,专门嘱咐不要告诉李阿姨。李阿姨是道希在文联的老领导老江的夫人,年轻时是中青报有名的美女记者,当年“青年鲁班”李瑞环的模范事迹,就是李阿姨负责报道的。后来李做了高官,曾专门把李阿姨接到家去坐坐,特别叮嘱说有事就来找他。李阿姨却从未找过这位高官,其人品让人敬佩。两老对道希和我亲如家人,李阿姨年事已高,知道了肯定惦记,医院看道希。天那么热,又那么远,担心她的身体吃不消。
朋友们都赶过来了,袁新人夫妇听志云说来了;小曹和小辉听李晨说后来了;老干局的一个局长和方华来了;我的妹夫志勤从老家赶过来了;老丁的大弟弟道明和老同学老彭从武汉来了;妹妹琳达也从美国飞回来了;小肖后来连医院,郑铮、李晨、小曹、郑飞也来了多次。江淮还是没忍住,把老丁的情况告诉了李阿姨,李阿姨一听,坚持要来,劝阻不住。她看了道希后,晚上失眠了,一闭眼都是他躺在病床上的样子。李阿姨后来隔几天都要打电话问问道希的情况,一直惦记着。老彭和另一位大学同学老柯隔几天都要来电问问情况。一个院子长大的发小韩云隔三岔五的来电话,一直牵挂。妹妹们和很多朋友也常来电问候。
叶梅当时在俄罗斯,回国后老丁已转到另医院的ICU,无法进去探视,就带着女儿胡嘉来到家中,感觉好暖心。
东红他们买了机票要来京探望,我坚持要他们退票。一个人病了,不要再劳顿其他人,心意我领了就是。
程小玲和徐柏林看后,坚信老丁不会死,能抗过去。小玲还提了个建议,要我每天记日记,把老丁的具体情况都记下来。这是个很好的建议,胡叠找了个本子,我开始了“丁道希病中日记”的记录,记下了他每天的血压、心率等指标和具体病情的变化,也包括哪些朋友来看望,哪些来电问候等杂事。后来在治疗期间,小玲也给了我许多专业的建议。
随后的几天,在不知所措提心吊胆中度过。我们排了班,24小时轮流在抢救室外值守。我和琳达是下午值班,因为只有下午2点可以进去10分钟探视,其他的就是等着交钱。看见从抢救室推出装在黄色袋子的“人”,直着眼睛看着推走了,心想:他也要这样被推出来吗?那种感觉真的太不好了!
两天后,我们问大夫情况怎么样,大夫说,他的一条腿已经跨出来了,看看接下来两天吧。
也就是说,他的一条腿已经从鬼门关里跨出来了!
大家才稍微的松了一口气。
我和琳达在外面说起了几个月前的美国之行。年,我们到美国在她那里住了一个月,那一次我们去了拉斯维加斯、达拉斯等地,在奥斯汀找到了欧·亨利的故居;年12月23号到年3月23号,我和老丁在美国休斯敦琳达家住了整整3个月。当时琳达来电要我们过去,我还有点犹豫。琳达说:乘着大哥现在还跑得动,你们过来玩玩吧。要是他以后走不动了,就来不了了。
现在看来,真是一语成谶。从美国回来不到4个月,他就遭此一劫。
在美国的三个月,我们走了不少地方,坐了东西加勒比海的豪华游轮,去了墨西哥、牙买加、开曼群岛、巴哈马的拿骚和自由港等地,那些地方都有一种遥远在天边的感觉;参观了佛罗里达西礁岛上的海明威故居;去了新奥尔良,寻找到了福克纳的故居;《飘》的故事发生地密西西比河畔的橡树庄园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路易斯安那州的赌场住了两晚,大家都小赢了一点点;还去洛杉矶道希的大学同学彭才秋家小住,老彭开车带我们到圣地亚哥游览了航空母舰和“世纪之吻”,自然还游览了好莱坞;LilyLiu请我们在比弗利山庄好莱坞明星常去的餐馆吃了很棒的西餐,老丁点的那块多刀的牛排,至今难忘,那是他最称心的饕餮?还在风雪交加的时候飞到了纽约,参观了哈佛大学、西点军校等,一路到了费城、华盛顿、波士顿,一直到了边境上的尼亚加拉,观看了举世闻名的大瀑布,这一切,成了他今生今世最后的快乐时光?所以,我要多配发一些他在美国的照片,那是他健康时的样子。
(年3月,老丁和琳达在美国路易斯安那州一家赌场)
琳达知道她大哥突发的病况后,哭了好几次。不过有了美国的三个月,她对她大哥,也算是没有遗憾了。
那几天,我和她都上火,嗓子疼,咳嗽,开了一些消炎去火的药。
医院的治疗令人郁闷。因为是在抢救室,每天都是不同的大夫,对病情的说法也不同。第九天的时候,我问一个女大夫,他脱离危险了吗?这是我最关心的问题。
女大夫说:应该是脱离危险了。
我当时挺高兴,晚上就告诉了几个朋友。
结果第十天,另一个男大夫说:谁说他脱离危险了?脱离危险了就可以从这个地方出去了!
你说,郁闷不郁闷?
而且,连续好几天,老丁的尿管都是红的。脑出血,跟这里有关系吗?每次问大夫,都得不到明确的答复。后来大夫说,他现在最大的问题不是脑袋而是膀胱出血的问题,怀疑里面有不明血块或是肿瘤。
尿袋里满满的都是血!
以前他的膀胱从未有过问题呀。
8月8号,进去探视时看到血尿不止。一个女大夫说请了泌尿科的大夫过来会诊,但不确定是什么原因,现在血色素已经很低了,需要输血。接着就是签字缴费,办理输血的手续。输了血,第二天老丁的精神似乎好了一些,眼睛睁开了,虽然不能聚焦,但也似乎认出了琳达,情绪激动,挣扎着想说话。
但大夫却跟我们说,医院不是强项,老丁这医院解决不了,建议我们转院。当时听了有点懵,我们抱着那么大的希望来到这医院,人没有脱离危险,还出现了新问题,还说不清楚是什么问题,最后要我们转院?老丁目前的情况,属于危重病人,医院会收?转院的过程中会不会出现危险?
而且,一直在这个抢救室治疗,进不了重症监护室,条件很差。每到探视的时间,只要戴个口罩都可以进去,几十个人一拥而进,乱哄哄的,就不怕交叉感染?有几次进去看到老丁居然光着半个身子露在外面,他是个昏迷中的危重病人哪,在空调房里,感冒就会要他的命呀!跟护士说了,护士满不在乎的说:他自己乱动的。
这就是他们的医德!
老乡老友文夫、兆华一直在找人托关系看能不能把老丁转进ICU,医院9月份要搬到新院址,ICU(重症监护室)和一些病房在逐步向新院址过渡,所以很难进去。
但愿我们医院的痛苦遭遇是因为他们要搬家处于动荡的特殊时期。
有一点是肯定的,医院开口赶一个没有脱离危险的病人,留在这里能好好治?那天探视后我们回到琳达住宿的和颐酒店,打了一通电话,咨询转院的问题,医院接受?路途上有没有危险?
医院人满为患,没有非常过硬的关系,谁会接受这样一个危重病人?
转院路途中,主要是担心车辆颠簸晃动影响头部,会不会再出血?
我说,这个问题可以解决,大不了路途中我抱着他,就不会晃动到他的头了。
几个电话打下来,跟预想的差不多,我只好把我的最后一张牌打出来。
医院的姜大夫打了电话。自从搬到这家公寓后,离公寓最近的三级甲等医院就是大家常去看病的地方。时间长了,我和内分泌科主任姜大夫互留了电话,加了
转载请注明:http://www.fbpcw.com/cxby/13345.html